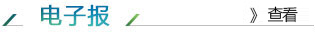娥姐是村衛(wèi)生室唯一的醫(yī)生,她發(fā)布的信息包括:通知兒童打防疫針,老人測量高血壓,貧困戶、殘疾人到村衛(wèi)生室檢查等。
轉(zhuǎn)了地球半圈,2019年春節(jié)返鄉(xiāng),我終于與一張張滾燙的鄉(xiāng)親面龐相遇。正如梁鴻教授說:“一個歸鄉(xiāng)者對故鄉(xiāng)的再次進(jìn)入,不是一個啟蒙者的眼光,而是重回生命之初,重新感受大地,感受那片土地上親人們的精神與心靈。它是一種展示,而非判斷或結(jié)論。”
暮色初降,車子在豫中郟縣陳村外公路上停住。爺爺生前開的琉璃瓦廠舊址上,新建了“富豪古建瓦廠”,廠名旁掛著“就業(yè)扶貧基地”的牌子。道路兩側(cè)滿堂堂的,煙囪、工廠、雕花灰瓦。通向村里的路口,竟也找了半天。
十年記者生涯,我一直關(guān)注各種新聞漩渦中的村莊,如“盲井村”;出國留學(xué)的課題也是關(guān)注海外邊緣村莊——墨西哥古老的瑪雅村、美國“活在現(xiàn)代的古代人”阿米什部落,以及印第安人部落……也許是我功利主義的嫌棄,陳村,這個中原默默無聞的小村,干癟而無新聞,一直被我漠視。2018年母親一場大病術(shù)后,無意中對我說起:“你知道嗎?陳村你出生的西廂房都快要塌了。他們說拆掉吧。我說不中,得留住,給楠楠一個念想。”
于是我決定返鄉(xiāng),去看看那個在我印象中沒有新聞的村莊。從2019年春節(jié)返鄉(xiāng)至今,這一年,我“臥底”卡車司機(jī)微信群,參加他們?yōu)橛鲭y工友的捐款活動,我還經(jīng)歷了有50年歷史的村莊小學(xué)被撤。喜怒哀樂,陳村的“新聞”,其實(shí)一直在延續(xù)。
“卡車協(xié)會分會長”
“‘老賴’已交錢,所有人停止打電話。”在近500人的卡車協(xié)會分會群里,商量對付欠錢的“老賴”是重要的命題,群主王曉偉在微信群發(fā)出語音指令,各種表情、文字、語音條閃爍,鼓勁的紅包標(biāo)語是“攻擊老賴人人有責(zé)”“一定要把老賴打倒”。
群主王曉偉和“老賴”電話溝通,動之以情曉之以理,無效后在群里發(fā)布“追討令”,詳細(xì)介紹“老賴”的惡劣欠債細(xì)節(jié),例如,“今天推明天,一拖再拖。就這樣推了一年多。”然后會動員大家行動:“卡友們上班了!主打老賴手機(jī)號,大家都把他標(biāo)疑似詐騙電話。”群里管理人員會提醒大家:“文明用語。大家切記咱是維權(quán)。別說攻擊的字眼。”直到追討條件談攏,群主會發(fā)布命令:“所有兄弟姐妹們注意了停止攻擊!聽總部命令。”
在微信群“臥底”半年,我目睹了十多起追討行動。而卡車協(xié)會分會長、卡車司機(jī)王曉偉,是我2019年春節(jié)返鄉(xiāng)深度接觸的第一個人。
那天,從瓦廠向南,步行路過干涸多年的水庫、新修的火車道,十分鐘就到400多口人的陳村。殘垣斷壁的老房子,很多都復(fù)墾成耕地,東一塊西一塊,點(diǎn)綴在房屋間,起起伏伏。
中原大地文化悠久,以陳村為中心,半徑10公里之內(nèi),就有蘇東坡父子“三蘇墳”、宋代官窯神垕古鎮(zhèn)、廣闊天地知青園等。而在我印象中,陳村的人們,世代在貧瘠的鹽堿地上刨食,種點(diǎn)玉米、花生、豆子,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悶聲不響。
離開多年,陌生的村莊,訪問什么?王曉偉進(jìn)入了我的視野。他四十出頭,作為微信群“美麗家園陳村”上百人的群主,是村里的能人。如果不是在地下賭場“輸了一個廠、一輛車”,他可能不需要現(xiàn)在這樣拼。如今,他貸款買了50萬元的卡車,從背著氧氣瓶的青藏線開到廣州往返跑運(yùn)輸。
王曉偉最在乎的,是微信頭像上印的身份:“卡車協(xié)會分會長”。農(nóng)歷臘月二十五,從廣州出發(fā),王曉偉把貨車開到陳村山腳下空曠地。第二天一早,他就帶領(lǐng)村附近的卡車司機(jī)們?nèi)f(xié)會總部河南某縣會師,參加春節(jié)聯(lián)誼會。
四五百名從各地趕來的卡友和家屬,在紅色簽名墻上寫下名字。音響轟轟、彩燈閃耀,搖臂專業(yè)拍攝。聯(lián)誼會的網(wǎng)絡(luò)直播地址一打開,各地卡友的點(diǎn)贊評論躍出。
“咱們協(xié)會的追討部,2018年成功地幫卡友們追回20多萬工錢,體現(xiàn)了抱團(tuán)取暖的精神。”卡車協(xié)會易會長發(fā)言致辭,“中國有3000萬名卡車司機(jī),互助組織很多。像我們一樣正規(guī)注冊、有2萬多人的協(xié)會,非常少有。”
“卡車協(xié)會專用酒”擺上桌,東北二人轉(zhuǎn)熱場,然后是歌曲《中國夢》。參加過湖南衛(wèi)視大咖秀的模仿者跳著杰克遜太空舞,煙霧噴出,變臉又模仿起獠牙惡鬼。
一面面錦旗被卡友們送上臺,前來主持的河南電視臺主持人略顯激動地解說著:“一方有難八方支援,卡車司機(jī)朋友們無論是遇到故障、翻車,還是亂收費(fèi),協(xié)會微信群消息一發(fā),卡友們能幫忙的都趕來,有時送一個零件,就解決了燃眉之急。”
王曉偉被授予了優(yōu)秀管理獎,水晶獎杯上是豎大拇指的圖案,他舉著給我拍照。在激昂的頒獎音樂中,卡車司機(jī)們從T字臺上場,領(lǐng)取榮譽(yù)證書,有的甚至還穿著厚絨睡衣。
聯(lián)誼會最高潮的環(huán)節(jié)是自稱“文化水平不高,只會說感謝”的司機(jī)點(diǎn)燃的。他叫東子,運(yùn)輸途中遭遇車禍,妻子不幸去世,留下年幼的孩子。協(xié)會一號召,卡友們給他家捐了4萬多元。分會長講這個故事時,現(xiàn)場鴉雀,然后是雷鳴般的掌聲。
“前一段卡車司機(jī)小輝夫婦去世,上萬卡車司機(jī)送行。他們出事的青藏線我也跑,缺氧難受。”同桌的王曉偉感慨,“外人很難理解卡車司機(jī)的心酸,有的運(yùn)蔬菜水果,一點(diǎn)不能耽誤,連續(xù)駕駛。有的運(yùn)危險化工品,要考專門執(zhí)照,處處小心。最氣人的是欠錢。”
卡友們說,現(xiàn)在的運(yùn)輸信息大多在網(wǎng)站獲得的,有時打個電話就成交,也不簽合同。貨主登記他們的身份證、駕駛證,裝貨運(yùn)到目的地,卸貨后才打款。有的借口貨品有損害等理由克扣工錢,甚至不給錢。
易會長解釋:“卡車司機(jī)文化水平大多不高,走法律途徑時間拖不起,很多都是一人養(yǎng)一家,月月要還車貸,成立追討部,就是應(yīng)廣大卡友之需。”
追討部設(shè)置專門的事實(shí)核查員,都是義務(wù)志愿。他們先核實(shí)情況、收集證據(jù),再打電話去跟貨主溝通。遇到“老賴”,就要用“集體轟炸”的土辦法了。
王曉偉琢磨:“最笨的辦法最有用,協(xié)會微信群動員司機(jī)們,都給老板打電話。老板每天接單子各種信息電話不敢錯過,一接就是要錢的,生意就沒法干,他們自然就想著還錢了。”
專門負(fù)責(zé)追討事務(wù)的余副會長,說現(xiàn)在遇到了新麻煩。被卡友集體騷擾過的老板,現(xiàn)在開始了智能設(shè)備“反攻”。
“協(xié)會負(fù)責(zé)人電話在網(wǎng)上是公開的,有的老板報復(fù)我們要錢的。用隱蔽號碼發(fā)消息打恐嚇電話,說什么要把你整的懷疑人生。我們壓力很大。”
聯(lián)誼會最前桌是協(xié)會邀請來指導(dǎo)的維權(quán)專家王金伍。王金伍義務(wù)支援卡車司機(jī),卻對卡車協(xié)會的追討辦法表示擔(dān)心。“合理,但是不提倡。電話集體討債,屬于法律的灰色地帶。還是要簽合同,拿好證據(jù)走法律渠道。”
王曉偉覺得王老師有道理,現(xiàn)實(shí)卻有眾多無奈。車貸分期付款,一個月要還1萬多元。一人開車,積勞成疾、腰椎間盤出問題,和“老賴”走法律途徑實(shí)在拖不起。
第二天,他去買了紅漆,把門上的校名描得紅紅的
“因今年縣城開辦4所學(xué)校,從農(nóng)村抽調(diào)200名教師,教學(xué)點(diǎn)只留1名教師,我們兩口子被調(diào)到中心小學(xué)任教,多種原因?qū)е聼o人調(diào)任趙樓小學(xué)任教,學(xué)校撤了。”2019年教師節(jié)前夕,9月5日凌晨,收到陳村趙樓小學(xué)校長李占永的這個微信,我淚流滿面。這所有著50年歷史,培養(yǎng)過北大、復(fù)旦學(xué)生,曾經(jīng)設(shè)立高中部的趙樓小學(xué),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。
李占永還給我發(fā)信:“看到一個家長發(fā)的朋友圈,很難過,群眾是需要教學(xué)點(diǎn)存在的。”他轉(zhuǎn)給我學(xué)生家長的朋友圈,上面配圖秋天蕭索的落葉,上面寫著:“我一個人在家哭得稀里嘩啦,兒子在學(xué)校哭,人生為什么有這么多的分別與不舍。”
現(xiàn)在想來,2019春節(jié)我對趙樓小學(xué)的探訪和返鄉(xiāng)直播,竟成了最后的留念。學(xué)校被撤,最擔(dān)心的事情還是發(fā)生了!
2019年春節(jié),我回到趙樓小學(xué),見到李占永。他說:“生存還是消滅?學(xué)生要是掉到個位數(shù),這里是不是就被撤了。”在11個人的村教學(xué)點(diǎn),李校長和劉老師夫妻是全部的師資力量。學(xué)校怎樣辦下去,這個問題總在心頭隱隱作痛。
校門上方的紅漆名,已經(jīng)斑駁難辨認(rèn)。進(jìn)門,迎面是一大片土地,荒草間有綠色植物拱出,李校長介紹是“鄉(xiāng)土教學(xué)基地”。右側(cè),排著一溜兒廢棄的教室,是上世紀(jì)60年代的老房子,刷著“教育必須為無產(chǎn)階級政治服務(wù),必須與生產(chǎn)勞動相結(jié)合”的標(biāo)語。
穿過舊房子,還有十幾間較新的房子。操場上,高高的桿子上,飄著五星紅旗。操場上,唯一的體育器材是一個乒乓球臺。
冬日枯葉蕭瑟,我端詳著空蕩的校舍。這里,曾開設(shè)初中和高中部,鼎盛時有幾百人。我的姑姑、叔叔等人都曾在這里上學(xué)。1977年恢復(fù)高考前,我父親19歲,是這里最年輕的物理代課教師。
看電視劇《大江大河》時,他感慨:“你想想,那時咱村的中學(xué)多厲害,恢復(fù)高考那年全縣考上本科的都不多,咱村考上好幾個,現(xiàn)在村里哪還有高中?”
人氣消匿,如今,這里的全部學(xué)生,一年級5個、二年級6個。李校長和劉老師每天滿負(fù)荷,交叉上課。教育局開會、日常校務(wù)需要處理時,一個老師外出,孩子不能單獨(dú)放教室不管。他們便把兩班合并在一個教室,一年級上課時、二年級做作業(yè)。
“一年365天,可以說350天都在這里。每天早上7點(diǎn)迎接學(xué)生,一直到晚上下學(xué)。真是‘一對一’輔導(dǎo),手把手寫字。成績不賴,去年有次鄉(xiāng)聯(lián)考,我們得個語文第一、數(shù)學(xué)第二。”
李占永19歲師范畢業(yè)時就分在這個學(xué)校,后來輾轉(zhuǎn)在多個小學(xué)任教。2015年他又回到了這里,擔(dān)任校長。教了近30年書,他獲獎無數(shù),指導(dǎo)的學(xué)生還得過全省奧數(shù)獎。
然而,村里一二年級學(xué)齡的孩子,有一半都不選擇在教學(xué)點(diǎn)讀書。
陳村是自然村,隸屬于1200多人的行政村趙村,這個小學(xué)是趙村唯一的學(xué)校。李校長分析:“現(xiàn)在很多家長打工,沒有精力照看孩子,做飯和接孩子耽誤做工。干脆送到外面寄宿學(xué)校、私立學(xué)校,收費(fèi)高一點(diǎn),圖個省事。”
教學(xué)點(diǎn)似乎被很多村民遺忘。包括我姑在內(nèi)的幾個村民,一臉迷茫:“你去教學(xué)點(diǎn)了?咱村那個教學(xué)點(diǎn)還在?”
王曉偉夫妻常年在外開車,兩個兒子分別送去縣里的私立小學(xué)和中學(xué)。“不想上教學(xué)點(diǎn),去外面公立學(xué)校又沒有戶籍,上不了。娃們從小學(xué)一年級就寄宿了,都是留守兒童。”
兒時調(diào)皮的玩伴小匪,現(xiàn)在是個常年輾轉(zhuǎn)在鄭州等地的吊車司機(jī)。他的女兒過兩年也要上小學(xué),我問他:“去不去村里的教學(xué)點(diǎn)?妻子和父母在家都可以照顧。”他斬釘截鐵說不,“感覺家里硬實(shí)的都把孩子送外面了,去村教學(xué)點(diǎn)感覺都是家條件不好的,人太少,孩子上著也沒勁兒。”
其實(shí)李校長一直攢著勁兒,努力聚攏村里的學(xué)齡兒童。教學(xué)點(diǎn)離家近、老師水平不差,本該是村民首選。他曾經(jīng)在村里貼喜報公布教學(xué)點(diǎn)成績,聯(lián)合村委會去做家長動員工作,去附近村人多的幼兒園提前宣傳等。
李校長心理明鏡似的,他甚至統(tǒng)計了2018年在村里辦婚禮的有8家。想著六年后,最多8個孩子入學(xué),還不知道幾個能來,他又有點(diǎn)神傷。
最大的考驗,是私立學(xué)校的搶生源大戰(zhàn)。隨著城鎮(zhèn)化發(fā)展,縣鄉(xiāng)的教育資源越來越集中,應(yīng)運(yùn)而生的寄宿需求,催生著私立學(xué)校如雨后春筍般冒出。
每年五六月,私立中小學(xué)到各村布陣宣傳。李校長形容:“那場面,就跟保險公司推銷一樣,上門送禮物,校車免費(fèi)接送,有的還承諾吃飯免費(fèi)。有的老師有招生任務(wù),招一個學(xué)生給幾百元。”
激烈的競爭中,李校長調(diào)整心態(tài),對自己說,最重要的還是教育見實(shí)效,孩子們的學(xué)習(xí)成績、精神面貌才是“金字招牌”。
李校長認(rèn)為,教學(xué)還得靠老師言傳身教,尤其是農(nóng)村孩子家庭教育基礎(chǔ)差,得因材施教。對于缺師資、缺設(shè)備的鄉(xiāng)村教學(xué)點(diǎn),多媒體教學(xué)資源,可以生動輔助音樂、美術(shù)等課程的教學(xué)內(nèi)容。
“教學(xué)點(diǎn)有國家的數(shù)字資源項目,都是免費(fèi)的。不過縣鄉(xiāng)中心校,多媒體資源更多,有配套老師指導(dǎo)。我們還是有差距,畢竟,教學(xué)點(diǎn)就兩個老師。”
從2001年開始實(shí)施的“撤點(diǎn)并校”政策,顯露的問題密集見諸媒體。很多學(xué)者認(rèn)為,撤點(diǎn)并校阻斷割裂了兒童與自然、家庭、村莊之間的關(guān)系。代表鄉(xiāng)村一部分的村落學(xué)校的消失,相當(dāng)于將已經(jīng)長在身體里面的器官或骨架突然拿走,加速了鄉(xiāng)村社會的解體和蕭條。而優(yōu)質(zhì)教育集中并校的“托拉斯”效應(yīng),讓鄉(xiāng)村教育愈發(fā)失去競爭力。
李校長說,在教學(xué)點(diǎn),他倡導(dǎo)陶行知的“教育即生活”理念,引導(dǎo)學(xué)生參與自我生活的改造。學(xué)生們在校園的菜地種芝麻、紅薯、油菜、玉米,收獲的食物共同分享。
李校長給我看他制作的視頻,帶孩子們?nèi)ド嚼锾で唷⒈孀R植物,介紹螞蚱的“保護(hù)色”,孩子們的笑容,純真燦爛如花。他還在網(wǎng)絡(luò)上尋找關(guān)于中華傳統(tǒng)道德、尊老愛幼等視頻,定期放給學(xué)生,進(jìn)行全方位素質(zhì)教育。
理想豐滿,現(xiàn)實(shí)卻可能骨感。李校長很擔(dān)心11人是“紅線”。鄉(xiāng)里現(xiàn)在20個教學(xué)點(diǎn),最少的就是11人。按照當(dāng)?shù)刂扒闆r,10人以下的教學(xué)點(diǎn)就可能面臨被撤并的風(fēng)險。
在教學(xué)激情和招生焦慮中,我眼前的李校長,把家安在學(xué)校,頭發(fā)油油的,嘴上起了火泡。第二天,我發(fā)現(xiàn)他去買了紅漆,搬來梯子,把門上的校名描得紅紅的。
如今,這個牌子成了絕唱。
麥秸垛、微信群和數(shù)字衛(wèi)生室
記得小時候,村子最南邊的小橋是個很有儀式感的地方。紋路精致的石磨盤、琉璃瓦裝飾的青龍爺廟,橋下是溪水潺潺,白鵝天歌。夏日的傍晚,村民們都湊過來,拿碗菜半蹲著吃,聊到天黑,這里是鄉(xiāng)村公共信息的傳播場所。
那時,石橋旁不遠(yuǎn)的晾曬場堆著迷宮般的麥秸垛,孩子們總是鉆來鉆去。場邊住著一戶人家,房子破舊不堪,孩子們也總是穿著寒磣,很害羞的模樣,很少到橋這邊見人。
多年后,在“美麗家園陳村”微信群,當(dāng)年害羞的孩子之一出現(xiàn)了,微信名“劉三”。他喜歡發(fā)紅包、推表情,很是活躍。親戚告訴我,父母去世后,青年劉三去哈爾濱打工,當(dāng)了上門女婿。路途遙遠(yuǎn),家里老人都不在了,一晃兒他十幾年都沒回村了。
微信群里,劉三喜歡做三件事:尋親、了解鄉(xiāng)情和匯報日常。“偉,你記得我嗎,我是你三哥。”“你那陶瓷廠還干著呢,沒放假啊?”“我干裝修活呢。”
有一次,他若有所思在群里發(fā)了句感慨:“娘在,家在。娘在,天在。”
當(dāng)年看《出梁莊記》,梁鴻老師分次去探訪被城市化進(jìn)程卷入的老家農(nóng)民工,了解他們“如何彎腰、躬身,如何思量眼前山一樣遠(yuǎn)的道路,如何困于勞累和幸福”。如今,通過村莊的微信群,陳村那些在西安、廣州、哈爾濱等地的大地親人,得以數(shù)字化聯(lián)結(jié),思想、情感、愛好躍然網(wǎng)上,鄉(xiāng)土中國的網(wǎng)絡(luò)新型“熟人社會”開始顯現(xiàn)。
給五保戶蓋的扶貧小單間,為啥他不住?養(yǎng)雞場離村太近夏天太熏怎么辦?村民熱議的公共事務(wù),通過微信群空間,得以讓信息充分流動,大家商討想辦法。有一年,村附近工廠爆炸,炸裂了很多村民的窗戶。村民相互統(tǒng)計家里損失狀況,去向有關(guān)部門舉報,最后這家工廠被取締。
陳村微信群,如今還有了“機(jī)構(gòu)入駐”,如村衛(wèi)生室。娥姐是村衛(wèi)生室唯一的醫(yī)生,也是群里的“公共知識分子”。她發(fā)布的信息包括:通知兒童打防疫針,老人測量高血壓,貧困戶、殘疾人到村衛(wèi)生室檢查等。
娥姐父親是村里的老村醫(yī),她兄妹幾人繼承父業(yè),都學(xué)了醫(yī)。對于村莊,她是醫(yī)生,更是普普通通的村民。她在微信群有時語音唱個戲,發(fā)布的信息也融合著兩種身份:
“鄉(xiāng)親們,天氣冷了,多喝熱水,防止感冒。”“室內(nèi)取暖防止煤氣中毒,不要在大柴火堆旁烤火。”“冬至別忘吃餃子。人生就像餃子,無論被拖下水,扔下水,還是自己跳下水,不蹚一次渾水就不算成熟。”
我去村衛(wèi)生室找娥姐,路上使勁回想,小時她爸爸給大家看病,喜歡用土黃色的紙包著幾顆藥丸,疊成三角狀,不過幾分錢,卻很見效。
童年記憶中昏暗光線的衛(wèi)生室,現(xiàn)在變得有點(diǎn)“高大上”。門口掛著“心理健康服務(wù)咨詢點(diǎn)”,進(jìn)屋,滿眼信息應(yīng)接不暇。四周墻上,貼著各式宣傳海報:“六道保障線保貧困人口縣內(nèi)住院零花費(fèi)”“健康知識問答”“縣健康扶貧遠(yuǎn)程問診流程圖”等。
娥姐說:“現(xiàn)在交通發(fā)達(dá),去縣里看病買藥都方便,來衛(wèi)生室的人少了。這里診療費(fèi)一次一元,大多是老人。不過現(xiàn)在,健康扶貧的工作忙得很。”
“搶當(dāng)貧困戶,嚇跑兒媳婦;拒當(dāng)貧困戶,榮宗展傲骨”,村里扶貧海報貼起來了,對口的人員都要行動起來。娥姐這小小的衛(wèi)生室,也是扶貧的重要陣地。
她統(tǒng)計的健康扶貧基本情況,包括村民和貧困家庭兩大類,具體分18個項目,包括高血壓、糖尿病、心腦血管、重性精神病人數(shù)等。
娥姐介紹:“這幾年上面有要求,衛(wèi)生室診治信息處方全部上網(wǎng),錄入省基層醫(yī)療衛(wèi)生機(jī)構(gòu)管理信息系統(tǒng)。我這不會用電腦,學(xué)了好幾天。來,看看你奶奶的健康記錄。”
我返鄉(xiāng)的那天,湊巧是村里一年一度搭臺唱戲的日子。這些年,村里已經(jīng)聚集了十幾家企業(yè),請戲團(tuán)的錢大多由他們贊助,1000元、2000元不等,豐富村民的文化生活。有的是主動交,有的需要村干部去“化緣”。今年,只有一家國有變電廠沒捐。
村干部跟我說,企業(yè)捐資贊助文化的傳統(tǒng),是我爺爺生前開辦琉璃瓦廠時定下的,延續(xù)至今。“那時咱村的廠,是大家的集體企業(yè),每年給村民分紅,現(xiàn)在都是私人企業(yè)了。”
站在琉璃瓦廠的舊址前,想著老人們給我說的村史。上世紀(jì)七八十年代,爺爺和村里幾名長輩,開煤窯賠了幾十萬,走南闖北又開始新的征程。他們?nèi)恼憬I過群羊,從陜西趕回過驢子。有一次,去包頭送花盆,回來買了100多匹紅棕馬。他們包了一箱火車皮,運(yùn)到市火車站。村里人去車站,把馬趕回來,浩浩蕩蕩,很是壯觀。
“馬很烈,訓(xùn)練了很久,給鄉(xiāng)親們犁地。”
爺爺劉保健,去世20年。我有時會想,如果他健在,會用怎樣的互聯(lián)網(wǎng)方式再運(yùn)回這一百多匹馬呢?也許只需要用手機(jī)點(diǎn)一點(diǎn)屏幕?
這就是我返鄉(xiāng)后看到的陳村,一切都那么波瀾不驚地運(yùn)轉(zhuǎn)著,似乎也說不出有什么特別的“新聞”。但是,陳村鱗鱗爪爪的動向也都是時代變遷中的標(biāo)記。